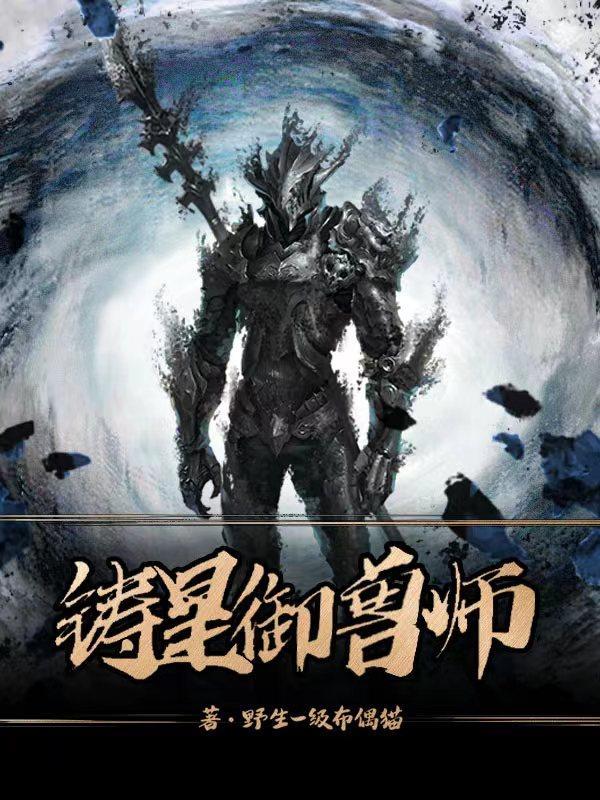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名犬图片及名字大全 > 第30章(第1页)
第30章(第1页)
边亭逃命一般,气势汹汹地下了楼。
出了kTV的大门,他在台阶上缓了好一会儿,被裹着大排档烧烤味儿的晚风一吹,人又清醒了。
这个时候,他有一些后知后觉的后悔,今天他是开车来的,因为那杯鬼迷心窍的威士忌,只能叫代驾回去了。
夜场的停车场边最不缺的就是代驾,边亭随便招了一个,自己上了副驾。
离开了夜店林立的地界,夜晚就安静了下来,车子四平八稳地往元明山上开,越是接近山腰,边亭的心情就越是沉重。
圆脸的代驾小哥是个外地人,第一次接上山的单子,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。他一会儿好奇住在半山腰上的人都是些什么身份,一会儿又打听这些别墅的价格,一路上兴奋得没完没了。
边亭心烦意乱,没有心情和他聊天,单手支着脑袋,懒懒看向窗外,一个字也不理。
到家了之后,边亭的糟糕情绪算是到了顶点,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,径直上楼回到房间,拉上窗帘,倒头就睡。
边亭将自己闷在被子里,缓缓睁开了眼睛,他不知该怎么解释自己今夜的反常,只能粗暴地归结于撞了邪,睡一觉等明天就好了。
可惜事情并不如他所愿,好好睡上一觉,并不能让他好起来,反而加重了他的中邪症状。
因为这天晚上,边亭做了个梦,在这个梦里,他见到这双眼睛真正的主人。
那个人分明近在咫尺,边亭每天都能看见他的脸,听到他的声音,随时随地和他说话,毫无顾忌地感受着他的气息。
但在他内心的深处,始终将他当成是一道远在天涯的影子,不可靠近,不可越界。一碰就碎。
这个人又从什么时候开始,以一种他不愿意承认的方式,进入他心里的呢?
边亭想,大概是十八岁生日那年,他在黑暗中,给自己点起了一根蜡烛。这是一场梦。
也正因为知道是在梦里,这次边亭既没有克制,也没有压抑,放任这个不该有的念头,在心里肆意疯长,吞噬着他的理智。
终于,边亭朝他伸了出手,手掌轻轻地贴上他的脸颊,指尖因为紧张,止不住地颤抖。
那个人不但没有反抗,没有呵斥,没有将他推开,反而是弯起眉梢,温柔纵容地望着他,眼里盈着一汪春水。
这个笑容他很熟悉,当他熟练地在靶子上射出十环时,英文考出不错的成绩时,又或者是看出报表上的错漏时,他总是这么笑着望着他,然后说上一句,“干得不错。”
边亭受到了鼓励,又或者说,是蛊惑,他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,捧住那张脸,小心翼翼地,吻上他含笑的唇角。
而后一不可收拾。
边亭长得冷,性子也冷,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太过浓烈的感情,也很难想象他会如此渴求一个人,一件事。
这个隐秘的欲望因为一次意外,被轰然揭开,他不知如何才能真正满足内心这种病态的渴望,只能不得其法地,一遍一遍,盲目且笨拙地亲吻那个人。
额头,眼睛,鼻子,喉结,一点点,一寸寸,他要在他的每一片肌肤上,都留下自己的印迹。
但是不够,还是不够,远远不够,他想得到更多。
只是那个人并不给边亭一点回应,从头到尾,他都没有说话,放任着边亭,在自己的身上为所欲为。
看似纵容,实则拒人千里之外。
就在边亭即将被这不堪的欲望逼疯的时候,那个人终于有了一点反应,冷冷地开了口。
“你为什么,要对我做这些?”他问。
就算在梦中,这声音也是边亭熟悉的清冽、冷峻、如冰层一般寂静无波。
对啊,为什么呢?
边亭浑身的热血冷却了下来。
“是不是因为…”
他揽过边亭的腰,一个利落的翻身,两人的位置生了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