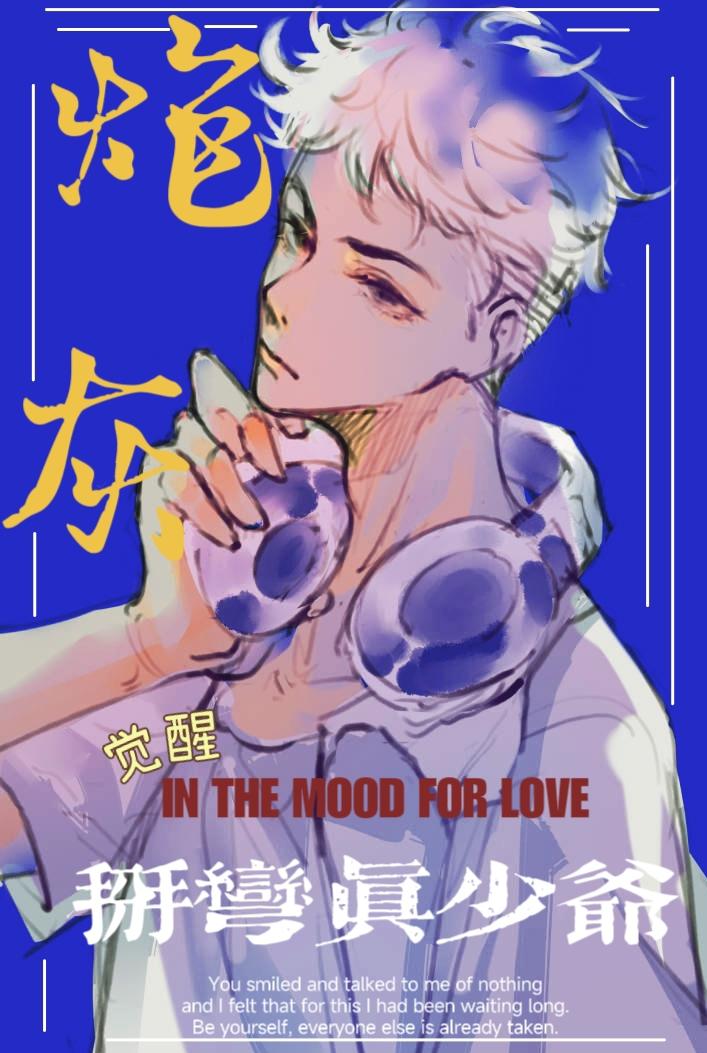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女扮男装权臣类 > 第54章 证据(第2页)
第54章 证据(第2页)
“哦,那我想请问,你的荷包放在何处?”
“自然是贴身放着。”
“若是贴身放着,被人偷了,怎么到现在才现?你又是如何现的?又是怎么笃定,就是我兄长拿的?”
听见许愿的话,程杰愣了片刻,而后道:“睡觉的时候,我把荷包取下来了,就放在枕头下面。早上我出去了一趟,回来就现荷包不见了,我一猜肯定就是被张越偷了,于是叫人一起去张越的营帐,果不其然,给抓个正着。”
程杰一番话,说的格外流畅。
这些话,他早就已经倒背如流了。
这几次下来,程杰也算明白了一点,张越是一个好唬弄的,可许愿不是。
若是说不出一个三七二十一,他还真不能把张越怎么办了。
“那意思也就是说,你不是一直在你的营帐,而是中间出去了一趟,你和我兄长一样,都是昨日来的,你怎么知道张越的营帐在何处?”
“我找人问的。”
“好,你是找人问的,那我还想问问你,营帐的划分都是统一的,张越如何知道你的营帐?难不成他特意去问了你的住处,而后去偷你的银子?程杰,你若是这个小偷,会不会觉得自己太蠢笨了?”
许愿话还没有说完,她看着程杰,继续道:“假如我兄长在无意之中知道了你的住处,又偶然得知你有银子,且看见你把银子放在了枕下,那我还想问问,一个营帐十个人,两个营帐二十人,加上来回巡视的人,起码有三四十个吧,人证呢?”
“是啊,人证呢?”
“我可以给这个兄弟作证,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,肯定是被栽赃的!”
“我也觉得是被栽赃的,这栽赃的手段也太低级了一些吧?”
“对啊,以后要跟这种人一起打仗,我还得防着人在我背后捅刀子吧?”
“别说,我也怕这个!”
……
听着四周的闲言碎语,程杰脸色立刻变了,“许愿,你就是在胡说!你有本事就证明你兄长没有偷东西!”
“这多简单。”许愿自信一笑,开口道:“程杰,你知不知道,有一句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?”
程杰有些懵,“什么意思?”
“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,这个荷包,最开始的作用,应该是放香料的吧?”
许愿轻轻捏着手里的荷包,又开口道:“以前我就现了,你这个人,总把自己当做谦谦君子,是以,会像女子一样,在自己身上放置香囊,你别否认,我刚刚一闻就闻到了。”
许愿说罢,把手抬起来道:“而今我摸过这个香囊,不知道那个兄弟可愿当一个证人,闻一闻我手上的味道和香囊上的香味,是否一致?”
许愿话落,当即就有人道:“我来。”
说过,那个人拿过荷包闻了闻,又闻了闻许愿的手,而后再去张越身边,最后他道:“张越手上没有香味!他根本就没有碰过这个荷包。”
听见这笃定的话,程杰脸色微白,倔强的开口道:“兴许,兴许是张越净了手。”
“怎么,你自己香囊里放过的东西,你自己都不知道?再者,以你所说,这个香囊我兄长才拿走不久,不妨我现在便净手,再让人闻闻,如何?”
许愿望着程杰,眼底全是冷意。
“你……”程杰不敢说话。
他也不敢真的让许愿去洗手。
因为,张越的确从头到尾都没有碰到那个荷包。
他即便再狡辩,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。
见程杰没说话,许愿把荷包直接丢了过去,开口道:“程杰,下次这种下三滥的把戏,还是少用为好,否则,见一次,我让你后悔一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