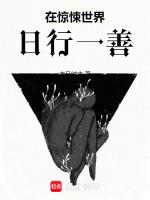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深爱无需多言 > 第二十七章 亲兄弟明算帐(第2页)
第二十七章 亲兄弟明算帐(第2页)
汪俊说,“奶奶,不贵。两个才一千块。”
其中一个长得很壮实的搬运工说,“你可捡了大便宜。我买了个1米5的,不带床板,就要了我六百。”
大嗓门婶子说,“做生意的,最怕老师和医生。”
汪俊哈哈大笑,“我终于明白难怪是什么意思了。惭愧!惭愧!”
黄远已经躺在了床上,因舟车劳顿,他的脸色十分苍白,他轻声问,“汪主任,熟食呢?”
汪俊一拍脑门,“当时尽顾着绑床垫了,忘了。”
这时,门外走进两个妇女。她们一个提着一口袋鸡蛋,一个手中捧着两把面条。还有一个男人落在了后面,他的手中,各提了一捆柴禾。有芝麻竿,有干柴块。
黄景瑜迎出门去,她非常感动,她的心中慨叹,“真是近亲不及远邻啊!”
黄坚不知是收拾粮食太忙,还是没脸见大家,又或是躲给工钱,他在之前跳骂了一顿之后,再没露面。
结工钱的时候,黄景瑜特地去叫黄坚,天已黑,她见么爸家黑灯瞎火,大门又锁着。她为了给么爸教训,就大声喊,“么爸,结工钱,结工钱!人家都等着呢!”
黄坚正在堂屋内喝酒,侄女的叫声,让他停止了咂巴嘴,和嚼花生的动作。他大气都不敢出,又怕侄女从猪圈屋转过去,他摸黑到了灶屋,关上了灶屋门。
回来时,不小心踢到了一个铁盆子,黄景瑜听到哐啷一声,紧接着三声猫叫,她不禁扑哧笑出了声,但她仍然没忘记把话传到。
她说,“么爸,亲兄弟明算帐,工钱我先帮你垫着,日后记得还我。我刚付了,1ooo块。”
谁知,她的奶奶在她身后,她抱怨,“你那么有钱,还惦记着要你么爸还钱。凭我和他住在一块儿,你应该倒给赡养费。”
黄景瑜吓了一跳,她转身见是奶奶在黑暗中鞠躬着背,心中甚是同情。但她对么爸的心,并没有变软。
她说,“奶奶,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养奶奶的那一份,与这个无关。”
老人见劝说无效,又去她大儿子的家里了。
黄远见母亲进来,她那驼着的背,和雪白的头,满是沧桑和皱纹的脸,让黄远不禁悲从中来,他一声“妈!”,把自己的心酸和泪水,都叫了出来。
老人的身躯颤抖了几下,她稳了一下之后,再蹒跚到黄远的身边。她拉着他的手,老泪纵横,“儿啊!你就是不听娘劝,这下晓得锅儿不是铁倒的了吧。”
“对不起!妈!妈,对不起啊!”黄远摸着他妈的手,微微颤抖。
在场的几个人无不动容。
黄景瑜正在烧了开水,汪俊准备离开,黄远又“哎呦哎呦”,痛得喊天叫地。
汪俊忙找到杜冷丁,给黄远服用下去。止痛之后的黄远,他的眼睛不断地在盯着卧室门口。
黄景瑜知道,爸爸又在想妈妈了。妈妈不是不来,她要明天再来。她妈妈虽然说了来,但心中的那道坎还没过。
这缘于过去的痛苦太为深刻,深刻得溶进了血液。人说血液是红的,那是因为吃了血情动物。而她们母子俩,在黄远给她们断了生活费之后,曾经两个月没沾荤腥。
她永远记得女儿黄景瑜说过的一句话。这时,电话响了,她一看,是黄景瑜打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