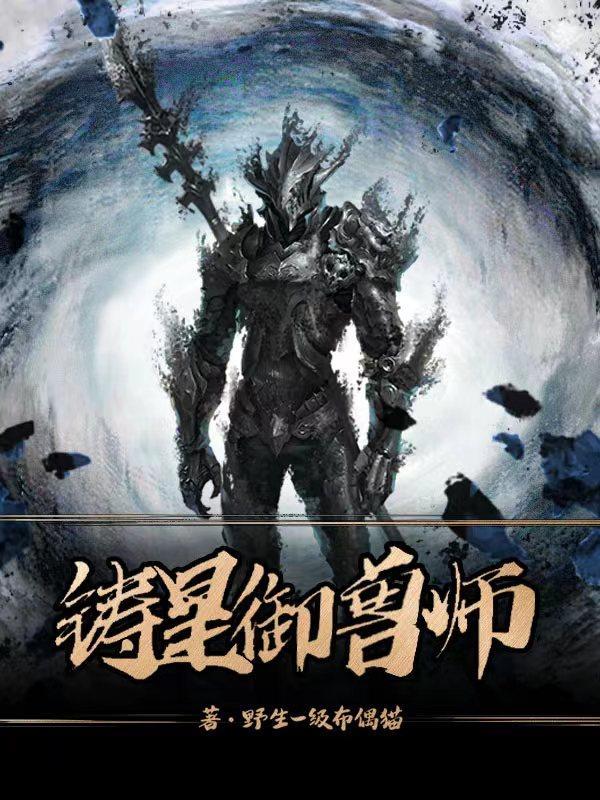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告别蝴蝶臂 > 第64页(第1页)
第64页(第1页)
李芷柔这次段考的决心也非常大,她抽屉里的课外书已经都不见了,物理化学的题也做了不少,经常缠着我问个不停,倒不是我平时成绩比她好,只是因为这个姑娘在和人交流的过程中大脑才开始转。
“莫希你看下这题。”她又来了。
我扯过半本书,开始看题目:“这个是不是用”
没等我开始说,她突然:“哦~~~我知道了”
总是这样。
更有甚者,两行字的题目,我一行字还没有看完,她就开始哦~~~了。
她说要在班主任走之前让他看看自己的力量,是的,她就是用的“力量”这个词。
尽管决心和结果并不相等。
就像我上次一样。
但我看好她,就如同我这次看好自己,虚妄的自负不该有,但切实的自信不算错。
路灯下的雪
从上次考砸到现在,时间过得太快,我记得从毛衣换到羽绒服还是上个星期的事情,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。
那天站在厕所里哭成花脸猫还历历在目,还好这么快我又有了一次可以重新再来,证明自己的时候。
当然这是和丁琪对比的,她经常说如果这次考研落榜她会伤透心,这一辈子都不再考了。
凡是话中涉及一辈子这个词,我都听的心有余悸,谁的一辈子可以这样随口并且肯定地说出来,一眼看得到边,没有任何改错的机会。
而丁琪整天都出于这样的压迫感中,她这些天掉头发很厉害,洗手池,梳子,桌子,地上到处都是,碰一下她的头都会扯下几根已经掉落的头发,已经到了我劝她去看医生的地步。
经常在家里给她扫头发捏头发的时候想,长大太可怕了。
丁琪一场试考了三年,已经被她爸爸那边的亲戚数落了很长时间,同龄人也走的比她快,事到如今,只有她自己的爸爸妈妈支持她,还有我。
我也只能一直用没有实际意义的话口头鼓励丁琪:“jtdoit!”
——这三个英语单词是朱宁告诉我的,他说我这个人很符合这句话。
从那时候,我就向自己宣布jtdoit已经取代“及时行乐”成为我的人生信条,虽然我并不觉得两者有什么不同,都是用来描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它只稍稍洋气一些。
段考的这一天,天空阴阴沉沉。
“小希,你是考语文吗,怎么不装语文书?”丁琪追到门口,拿着书问刚想下楼的我。
“哦哦,怎么偏偏忘记这一本。”我两步走过来拿过书,边塞进书包边下楼。
走出楼道的那一刻,我把手插进棉衣的口袋里,一拍脑门,忘记带饭钱了,又气喘吁吁折回去拿钱。
这一大早就开始失魂落魄,丢三落四,真不是个好兆头。
到了学校,直愣愣地走进了考场,呆坐着盯着桌子上的纹路很久,直到一个同学过来,她是我以前32班的同学。
“莫希?你是找我还是?”她弯腰问我。
“”我静止了很长时间,像是一个思想退化的老年痴呆症患者,慢慢地反应着。
叮!进错了考场!
羞愧难当的是,这一层的考场都几乎算是倒数,我们班除了我和李芷柔在二楼,其余人都在一楼,那个昔日同窗惊奇地问我:“你上次考了多少名,怎么会分到二楼?”
“嘿嘿我上次考得不好”我敷衍地笑着,手上还一边紧急地收拾东西。
于是在考前十分钟寂静的走廊上,一个女生拎着拉链还敞开着的书包,中途从中掉下几支笔,一个利落的刹车俯身去拾,慌慌张张又跑进走廊尽头的另一个教室。
我勉强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的时候正正好写完语文试卷,画上作文的最后一个句号,等老师收上我的试卷,一把抓起书包就赶回家,想要中午早点睡一觉,下午可以清醒些。
并没有结束,中午醒来更是昏昏沉沉,不知道怎么飘进的学校,刚坐在位子上就听到班级里的音箱喇叭喊:“38考场有人遗落一部手机,黑色触屏,请速来教务处认领,请速来教务处认领。”
我摸摸口袋,翻翻书包——那是我上午落在讲桌上的手机。
满头大汗从教务处拿手机回来,看到考场里晚到的同学竟然撑着伞,于是发现,外面下雪了!我没带伞!
我的考号又是4号,坐在窗户旁边——多么不吉利的一个数字。
雨天是我的倒霉日,雪天不会也是吧,我在心里默默哭诉。
又甩甩头睁大眼睛安慰自己:“莫希,这些征兆都不算什么,一个在二十一世纪接受科学素质教育的人怎么可以相信这些,我们是勇敢的唯物主义者。”
唯物主义这个词,还是我翻丁琪的政治书学来的。
李芷柔也在这个考场,不过离我有点远,我转头看看她,她正焦急地在草稿纸上一遍遍不停地写着什么,我猜是她讨厌的那些复杂的公式,因为数学没有什么好写的。
我把脸转向窗户外面,越下越大块的雪花摇啊摇,缓缓飘在空中,块头虽然大,但很稀疏,玻璃窗户上也沾上了一些,很快化掉了,我集中精力利用没化的那几秒清晰地看到了雪花的形状。
两位监考老师抱着试卷带进来了,其中一位是语文老师董冬冬。
在数学试卷上写完名字和班级,董冬冬看见了我,对我微微笑一下,开始在黑板上写考试时间。
我瞄了一眼窗外飘飘扬扬的大雪,想起李芷柔那天说的“下雪必刮北风”。
下雪必刮北风,此刻一点风都没有,教室里安静极了,窗外的校园里也静谧得好像可以听到雪落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