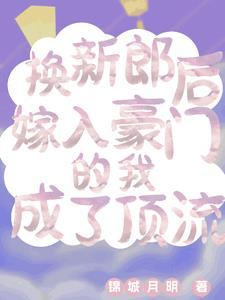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重生桑婉 > 朕是你爹(第2页)
朕是你爹(第2页)
啪!
白玉心将筷子拍在了桌上,低声斥道,“红豆,你几时生出这种心思来着?!姐姐与皇上难得见上一面,我这时候去做这种事,可还算人么?!何况,我本是不愿承宠的。”
红豆却忽的跪了,仰头哀求道,“小主,您不能这样下去。白家花了大笔银子,疏通关节,送您入宫,便是指望您能得皇上恩宠,出人头地,光耀白氏门楣。您如今就躲在长春宫里,仰赖着贵妃娘娘过这闲散日子。贵妃娘娘好一日也罢了,倘或有朝一日贵妃竟坏了事,您又要如何自处?”
“住口!”
白玉心怒不可遏,竟抬起一手,红豆便闭目等候耳光落下。
她是个温婉淑雅的性子,从未打骂过下人,看着红豆那略带着几分稚气的脸,终究还是放了下去。
“红豆,我不知走之前族长交代了你什么,但既然你是跟了我一道进宫,就最好认清楚到底谁才是你的主子。今日这些话,我听过也就罢了。但倘或日后再让我听着,仔细我就全数告诉贵妃姐姐。”
白玉心口吻冷厉,注视着地下跪着的红豆。
白玉心明白,这是族长安插在她身边的人。
看着抽噎的红豆,她叹了口气,缓了口吻,“红豆,我知道你也算是一心为我着想。但这宫里,事情没有那般简单。你瞧贵妃姐姐那样显赫的出身,皇上待她好了,那些人便虎视眈眈,整日只想着如何谋害长春宫,何况我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人。再则,且不说皇上眼里真的没有别人,便是侥幸我能得上些恩宠,我资质如此平常,不过三夜五夕,皇上就会把我抛之脑后。待到那时,贵妃姐姐也与我生分了,我岂不是坐等那些人把我嚼的连骨头渣子也不剩么?”
话至此处,她盯着红豆的眼睛,一字一句道,“最要紧的是,穆姐姐待我情谊深重,我不愿为了那浅薄的恩宠便辜负了她。往后,这些话决不许再提。”
红豆听着,便磕了头,“小主交代,奴婢都记住了。”
白玉心方又准许她起来伺候。红豆赔着小心在旁布菜,又瞧着她的脸色,小声道,“皇上今儿高兴的很,听说贵妃娘娘的哥哥在西南打了胜仗。”
白玉心耳里听着,赫然想起那日自己躲在乐志轩窗子后面,瞧见那人时的情形。
他昂阔步,器宇轩昂,英气勃,是她平生仅见的好男子。
他是弋阳侯世子,而她只是个不会有宠的嫔妃,注定了一生困在这红墙之内。
用过晚膳,黎谨修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,在明间炕上倚着软枕看折子。
穆桑榆便坐在一旁,看着一卷医书。
豆蔻坐在两人之间,玩着一只九连环。
宫女送了茉莉花茶上来,袅袅白烟将茶香散满了屋中。
虽是无言,却也算得上静好。
时辰一点点过去,豆蔻已忍不住哈欠连连。
穆桑榆放下了手中的书,看向黎谨修。
黎谨修已摘了冠,只留一支乌木钗挽着髻,余下的便垂在肩上。
他脱了外袍,只穿着一件牙白色绸缎单衫,宽阔的胸膛微微起伏着,全神贯注的看着奏章,丝毫没察觉周遭情形。
烛火在他高挺的鼻梁上洒了一层柔光,令那平日里冷硬的五官柔和了许多,却更显俊美如玉。
平心而论,黎谨修委实称得上一句丰神秀逸,龙章凤姿,莫说帝王之尊,仅凭这一身皮相便能迷住无数姑娘,也莫怪当初京城多少权贵千金挤破了头想进宁王府。
指婚的旨意传至弋阳侯府时,穆桑榆还被闺中的姐妹们好一番嫉妒。
时至今日,穆桑榆却有些迷茫,她当初的情思到底是那本书要她去爱这个男人,还是自于她真心的情感?
太皇太后的意思,她懂得。
只是,她心底里惧怕着和他肌肤相亲,一夜欢情之后又会怎样,她不敢去想。
“皇上,”穆桑榆轻轻开口,“时辰不早了,豆蔻困了。”
“嗯。”
黎谨修抬眸,看了一眼桌上的鎏金珐琅自鸣钟,已是亥时二刻了,便道,“果然晚了,是该就寝了。”
话落,他便看向穆桑榆。
她没有看他,只是低头抱着孩子,豆蔻伏在她怀中打着瞌睡。
罢了。
黎谨修起身,吩咐李德甫取来外袍,“朕回养心殿去,你们也早点安歇。”
言毕,他披衣离去。
穆桑榆送到门上,看着皇帝的仪仗没入沉沉夜色之中,方才转身进去抱了孩子进寝殿睡觉。
黎谨修乘着步辇,穿行在月色之下。
李德甫百思不得其解,禁不住出声问道,“皇上,您这是何苦……好容易太皇太后娘娘今儿给了这个机会……”
黎谨修沉沉说道,“她不想留朕,朕看的出来。早些走了,免得她又拿孩子当借口。”
话出口,他只觉心头苦涩,她对他似是还有情意的,却又那么的飘忽不定。
他想要尽力的捉住什么,却又无处着手。
已是深夜,寿康宫却仍旧灯火通明。
蒋太皇太后已换了寝衣,却还不曾就寝,只是等着消息。
藏秀匆匆进来,向她摇了摇头,“禀太皇太后,皇上回养心殿了。”
蒋太皇太后只觉气不打一处来,“这个废物孙儿!到头来,还是要哀家这老婆子亲自出手不可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