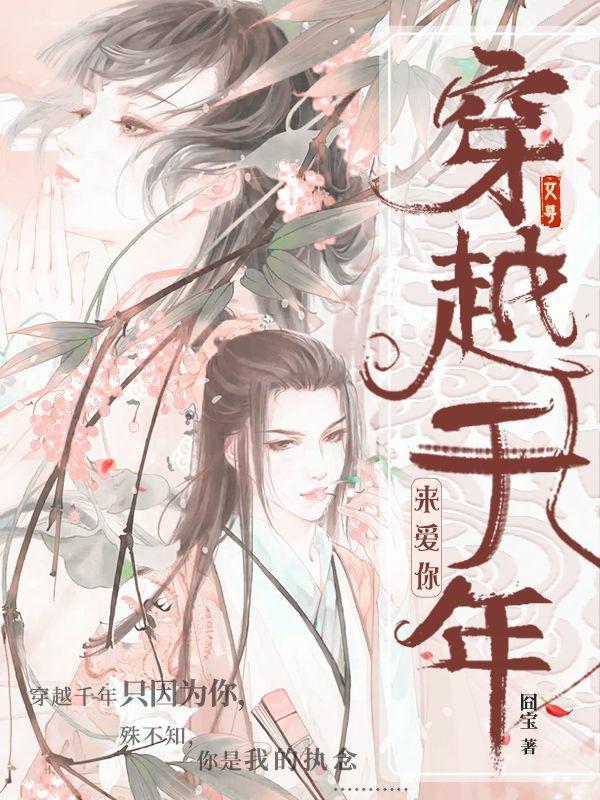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大明景泰朕就是千古仁君免费 > 第49章 给皇太后送去(第2页)
第49章 给皇太后送去(第2页)
“陛下口含天宪,答应过我的……”吴通声音凄厉,却不会死,因为朱祁钰只砍他一条腿,不断挥剑,把他这条腿剁成肉泥,狠狠折磨他!
“答应个屁!天宪也救不了伱!说!谁指使你的!”朱祁钰挥剑劈下。
“说了又如何?陛下敢杀她吗?”
自知九族必死,吴通反倒不怕了,嘲讽地看着朱祁钰“是圣母皇太后,圣母皇太后交代臣的!陛下,臣告诉你了,你敢报复吗?”
朱祁钰满脸是血,喘着粗气停下了劈砍,死死盯着他“有何不敢!拖下去!把他九族抓来,砍成肉泥!喂狗!”
啪,朱祁钰把剑丢在地上。
颓然坐在地毯上,气喘如牛,抹了把脸上的血“冯孝,你说朕是皇帝吗?”
“连一个将死之人都敢嘲笑于朕,他说得对,朕就算知道真相又如何,敢报复吗?”
“妻子被害死了,丈夫都不敢报仇,真他娘的窝囊啊!”
“传朕旨意,吴通等八人,使毒药谋害于朕,诛其九族,剁成肉泥,蒸成包子,给皇太后送过去!”
冯孝脑门死死贴在地毯上,不敢吭声,等皇爷说完,才应声“奴婢领旨。”
“回来,再传旨,太医院所有太医移交北镇抚司,查,查查谁还有谋害之心,谁是庸医?现者满门抄斩。余者打去惠民药局,三年为期,以观后效。”
朱祁钰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,总要给活着的人留点希望,不然他们去了惠民药局,照样祸害老百姓,老百姓求告无门,反而给了他们作威作福的机会,还不如现在直接宰了痛快。
朱祁钰叹了口气,从地上站起来,调整心态“收拾收拾,对了,把艾崇高留下,朕有事要问他,去吧。”
坐回御座上,心态平复了,气大伤身,原主对皇后感情很深,被影响了。但亲手杀了吴通,他明显感觉到浑身轻松,原主的执念消失了,以后朱祁钰就是他,他就是唯一的朱祁钰。
他吐出一口浊气,整顿太医院、整顿内宫、整顿禁卫、锦衣卫、东厂,才能安全,任重而道远。
兴安被拖了进来,和他一起的还有曹吉祥,他居然还活着。
“谢陛,陛下隆恩!”兴安冻得抖,在寒冷面前他也顾不得颜面了,缩在火炉旁瑟瑟抖,拖他进来时给他件衣服遮丑,省着污了圣目。
“大珰,何苦来哉啊。”
兴安叩“奴婢已是白身,当不起大珰的称呼,还请陛下切莫羞辱奴婢。”
“朕自问对你不错,司礼监由你掌印,位极人臣,可你是怎么回报朕的?呵,不提也罢!兴安,朕问你几件事,若从实招来,朕给你个痛快,决不食言。”
兴安面皮一抖,就知道这几个问题回答了也是死路一条。可他是太监,没有亲人,能体体面面去死,总比受尽折磨再死好得多吧?
“您问吧,奴婢知无不言。”兴安亲眼看见皇帝如何折磨朝臣,他这个阉竖,若再不识相,死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
“住在永安宫的聂姓宫女,去哪了?”朱祁钰问他。
兴安苦笑“陛下,根本就没有什么聂姓宫女,那老太监为攀龙附凤,顺杆爬说出来的。太上皇,就是皇太后所生的,奴婢可以作证!”
“不可能!”
朱祁钰不信,冷笑两声“你丧尽尊严,也不肯咬出太上皇,可见你是他的忠狗,这等事朕问你也是白问,朕问你第二件事,司礼监里,有多少是太上皇的人?”
“陛下,您只盯着太上皇,却被人钻了空子!”
“您认为司礼监都是太上皇的人,错了,您御极八年,太上皇影响力又剩下多少?”
“您认为的太上皇的人,其实都是内阁的人!”
兴安满脸悲戚“奴婢临死前,想劝您两句,报答您信任之恩。”
“您大杀四方,看似局势在握,其实是被当枪使了。”
“您削了奴婢的权,谁来接替奴婢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呢?”
“您削了勋贵的权,谁顶替勋贵的位置呢?”
“您杀了高谷、江渊、王翱,又是谁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呢?”
“您杀了襄王,又是谁顶替襄王的位置呢?”
“臣权是皇权的延伸,是陛下您掌控天下的触角。”
“您杀空了朝堂,产生的权力真空,便宜的却只是继任者!但损害的却是您的名声!”
“陛下,您怎么确定,新上来的官员一定听您的话?难道不听话就还继续杀吗?”
“您这次杀个措手不及,尚能杀上几人,可下次呢?内阁还会任由您胡闹下去吗?”
“不能的,您杀了宁阳侯,便彻底把勋贵推到了内阁去;杀了襄王,又自绝于藩王。”
“等内阁掌握了司礼监,文官彻底形成无孔不入的集团,皇权就真的衰微了,您手里就什么都没有了!”
“您想靠范广的一支团营翻天吗?不可能的,陛下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