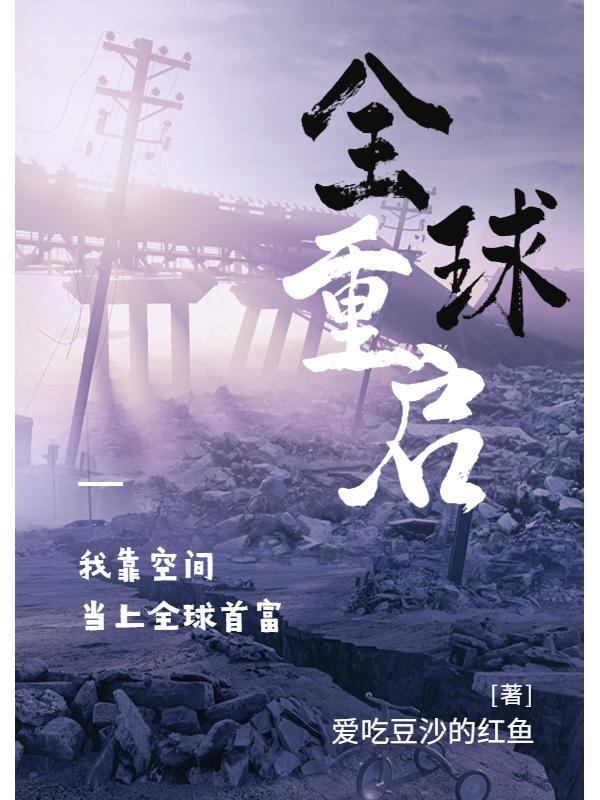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梦南轩文言文翻译 > 第27章(第2页)
第27章(第2页)
安静地等待着他的郑南轩,有些想挣脱他往前跑的陈子芹,在草地上,苍穹下,人群中,看起来小小的。
虽然风有些冷,太阳却照在他们身上,他离开成片的树荫走向他们,也走到了阳光下。
植物园的儿童游乐场大约是这两年改建的,以往这里好像什么也没有。攀爬网、攀岩的斜坡连着木架和滑梯,孩子们热衷于在此处爬上爬下。
过去不爱攀爬的陈子芹,在oT课上学会了攀爬以后,也能在这个游乐场玩一些时候了,尽管她还不能像其他孩子那么机灵,不会自觉地排队等候在攀爬网的入口,也很难现因为自己太慢而催促她的别的孩子是在和自己说话,但她也没有过去那么显眼了,混在一堆孩子里,还算可以和他们用差不多的方式玩耍了。
因为在密闭的玩乐区,除非从滑滑梯那里下来,否则陈子芹不会走丢,郑南轩终于可以稍微看一下别的地方了。陈青筠站在陈子芹玩耍的攀爬网下,抬头看着她,郑南轩将目光停驻在他修长白皙的脖子上,在还没转开视线时,陈青筠转头过来。
“除夕你回家过吧?”
“嗯,不过吃过晚饭会回南城睡。”
除夕那天是七七,陈青筠和陈子芹不能过年,做完法事后应该就会待在家中。
“就在你家里睡一晚上吧……初一不还得拜年吗?”
“没什么可拜的,不去也行,我爸那边亲戚都是年初二晚上聚的。”
和带丧的人住在一起,平日还不觉得有什么,到了节日,应该会格外的不好吧陈青筠心里也免不了这样想。如果春节他们还住一起,小姨和小姨丈会觉得不吉利吧?
“要不春节你住回家里?”
“我以前春节也是这样过的,不到年初三就跑了。我爸妈早就放弃我了。”郑南轩笑了笑说。
“以前这么些年……都这么忙的吗?”自从和书净结婚以后,每年年初三的家族聚会上,陈青筠从来没见到郑南轩出现过。
“不忙,就是不想待在家里。”郑南轩看着陈青筠,说。
如果问他是不是因为想避开自己才不愿在家中待着,是不是太自作多情?陈青筠最终也没有问。
直到今天,他也不知道当年的郑南轩为什么要和自己绝交。那天晚上他们确实吵架了,他的语气确实很不好,可是那只是他的心情,他的秘密,绝对无人知晓可南轩在那之前就疏远了他。
现在这样住在一起,他们也像所有成年人一样,对过去的芥蒂闭口不谈。
如今南轩主动提起,他也不敢问。他怕得到他心中猜测的那个答案:因为厌倦了照顾你,因为想交别的朋友,因为你的友情太自私,让我感觉太沉重了。
那自私的情感和贪欲,被友情的外衣裹得严严实实的,一层又一层,当然会让人感觉越来越重。他好不容易都丢弃了,埋起来了,平平整整,不露痕迹,自是再也没有勇气把它挖出来。
那是与和书净完全不同的情感。与书净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,点滴累积的记忆,拼命地堆叠在那被埋葬的见不得光的东西上。但陈青筠知道,那东西是烈火,是深渊,只能摁下去,不能让它浮起来。
陈青筠没敢再看郑南轩,他跟随陈子芹来到滑梯的附近。他深知书净的离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生活上、精神上的坠落和痛苦。
还有,从今往后漫长的日子,他都要靠自己把那深渊中的烈焰掩埋了。
腊月廿八下午,书衡和母亲回到青筠莞城的家中,和青筠一起,备下做七七需要的器具和食物,等到子时,迎接做法事的师父上门,开始做七。
七七是最后一个七,也是头七外最隆重的一个七。因为公墓夜间不能进去,所以七七在家中做,从子时开始,需要师父念经做法几个小时。
书净的遗像被取下来放在案上,案上摆满了各种食物烫好的鸡、肉丸、鸡蛋肉卷、祭奠用的饼干、炒米饼、白米糕、各种水果、干果。香炉放在正中,塔香燃在两侧,**的火烛在两边的烛台上点着,还有燃着灯芯的油灯,家中所有的灯都亮着,室内前所未有地明亮,黑白的遗照折射出了彩色的光。
从法事开始,烧纸桶里的金纸没有停止过燃烧,一沓一沓的金纸在火光当中变成了薄薄的暗红的灰,褪去火色,成了浅浅的灰,最后成为了深灰色的死灰。死灰沉入桶底,燃烧的灰浮在表面,层层叠叠,好像人那样高的金纸,烧完了以后,轻飘飘的灰堆积在底部,也不足半桶。
不过四十九天,青筠看着火光中书净的遗像她像离开了一个世纪。
活着就是这么残忍的事情吗?像纸桶里的金纸,纵有万吨重,也必须把它们变成轻轻的灰,压缩在记忆的角落,曾有的爱和温情,再也摸不到它们的形状。
像他的母亲,像书净。她们离开了,他却依旧不能停泊。他在深不见底,广不见边的漆黑中,漂浮在海面上。
“我要活到一百岁,我要比子芹死得晚,这样,她就一世也不会被人欺负啦。”
怎么办呢?他可能要代替书净,拼命地活到一百岁了。
清晨来了,遗像上,书净脸上的彩光褪去了,法事结束了。人们在太阳升起以后离开了屋子,陈青筠静静地坐在香案前,等待蜡烛和香火燃尽。
腊月廿八晚上,郑南轩带着陈子芹入睡了。青筠在下午就出门了,去办书净的七七,要到除夕中午才能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