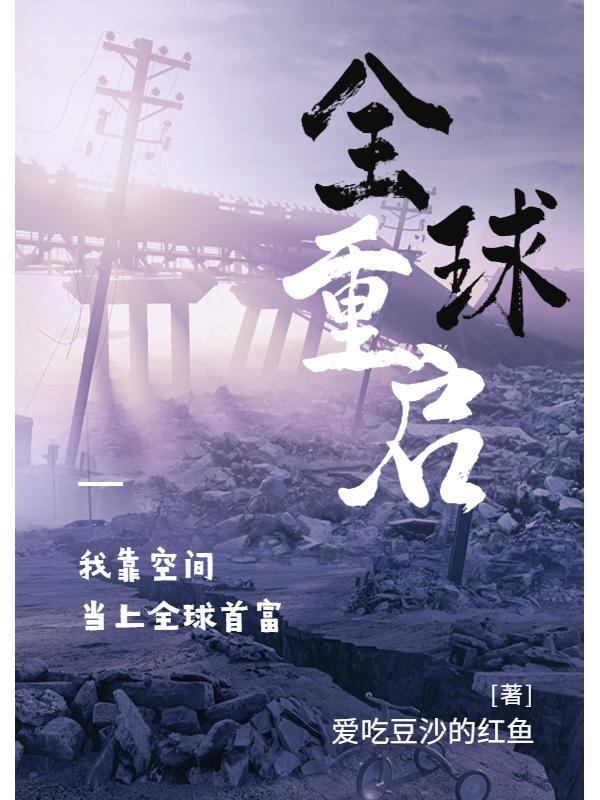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向他坠落讲了什么内容 > 第39頁(第1页)
第39頁(第1页)
十多分鐘之後霍岩山才鐵青著臉走出來。薛伍上前聽候吩咐,卻被告知「不用管他」。
「那……要不要叫軍醫?」
「用不著,他反省完了自己會走。」
「是。」
薛伍嘴上答應,心裡其實有點擔心白項英的狀況。因為以往霍岩山教訓他也都是打完了罰跪,跪完了自己找軍醫,但事實上每次都是跪得半死不活才放出來。白項英又是個不會喊疼的,經常是上一秒看著沒事,下一秒忽然直挺挺栽倒下去,這讓他不禁擔心哪天對方會不聲不響暴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。
待霍岩山走後薛伍進到屋裡,見白項英姿勢端正地跪在「老地方」,看樣子好像是沒什麼嚴重的外傷。至少沒見血,只有嘴角有點破損的痕跡,大概是耳刮子抽的。
第31章29最後的淨土
「白副官,你要是撐不住了就說。」薛伍公事公辦地叮囑一句。
白項英木然地抬頭,右手支地慢吞吞從地上爬起來:「謝謝,我沒事。」
薛伍見他自行起身,知道這回霍岩山沒有叫他罰跪:「司令說反省完了可以出去。」
「是……我緩緩就走。」
霍岩山是沒怎麼罰白項英,除了剛回司令部時挨的那記窩心腳。本來就是跪著挺罵,那一下直接把他踹翻在地上,緩了好久才喘過氣,緊接著又被帶進刑房。
白項英已做好掉層皮的準備,沒想到霍岩山把薛伍支出去說要親自動手,但實際上也沒有真的上傢伙。後來他知道了,他要他馬上回市里賠罪,因此不能弄得太難看。
齊繼堯果然把便衣隊的事告訴了霍岩山,想必講得十分嚴重,而後又描述了他在酒館裡的「所作所為」。霍岩山瘋了似的罵他,說他是坑貨,不是抬舉,存心想害死他。
「我反覆叫你對他客氣!他現在是政治處監察員,那是什麼地方你不知道?我見了他都不好說什麼,怎麼,叫你陪個笑臉委屈你了!?」
「就你的臉是臉,就你的身段金貴?平時沒見你多清高,專挑這種擅耍陰招的小人甩臉子,你這發的是哪門子瘋?啊?」
「姓齊的見財眼開,嗜賭愛嫖,要討他歡心再容易不過,你倒好……媽的,你甩給他的巴掌最後通通都要回到我臉上來!」
白項英一言不發的跪著。他不知道齊繼堯在電話里說了什麼,也許是添油加醋,也許是無中生有,但這些都不重要了。他說他端架子,不識好歹,以下犯上,說什麼都行。這裡沒有可供他辯解的地方,橫豎他都要去賠罪,把白天逃過的恥辱全部領回來。
是的,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,他不過去還債罷了,只有叫債主滿意才能換得長久安寧。
霍岩山罵的都是事實,他是捅了婁子,給對方惹來大麻煩,而且是本來可以避免的麻煩。可時間回到兩個鐘頭前他還是會那麼做,別無選擇。
恥辱算什麼,一切都不會比那個時候更糟糕了。十年前霍岩山將他從絕境中拉起,在為他披上保護殼的同時也用的枷鎖將他禁錮起來。十年後有人不自量力地想要打破這枷鎖,殊不知開鎖的鑰匙一直在他自己手裡。
經歷過絕望的人大多堅硬和麻木,更不會在乎那些無關痛癢的目光。沒有誰可以真的拯救他,他也不需要所謂的同情和憐憫,可霍今鴻是特殊的。
即便所有人都知道他的「真面目」,至少在那孩子眼裡自己可以是個人。
那眼裡有他的痛,也有他所剩無幾的淨土。
。
白項英出刑房後沒有在司令部逗留而是回了霍宅。
霍岩山讓他收拾好了等著,小孫會準備好東西交給他,而後他就帶著東西去齊繼堯在市裡的住處,當面賠罪。
東西無外乎就是菸酒古董之類的賠禮。齊繼堯嗜酒,平時有抽大煙的愛好,最近還聽說迷上收集東洋古董,而家裡正好有一些日本人送的「好貨」。
霍岩山沒有提付聘背著他走私日貨的事。依照他的性子要是知道了必然會當場追究,沒說就是不知道,看來齊繼堯沒有拿此事要挾他們的打算。
仔細想想對方自己也未必乾淨,本來走私之事一旦追究起來就不止牽扯到軍方人員,市政廳和工商會議所的某些高官恐怕也難逃干係。
回屋後白項英問勤務兵要了點冰塊,用布包著輕敷在傷處。霍岩山的那一巴掌沒令他破相,只在嘴角留下一塊「恰到好處」的裂口,像是故意給人看似的。
嘴角凍得發麻。他放下冰塊,猶豫片刻還是上樓洗了個澡。脫衣服的時候從鏡子裡看到自己胸前的淤青,這才想起除了臉上那巴掌以外還挨了霍岩山實甸甸一腳,不過現在已經不怎麼痛了。
這是他頭一回全須全羽地從刑房出來,為了接受接下來的第二次懲罰,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。
洗完澡小孫已經在會客廳等候,把東西交給他,順便問了句是給誰的。
白項英想既然霍岩山沒有提齊繼堯,那大概是不想讓旁人知道這事:「市政廳的一位官員,司令的舊識。」
小孫也沒往下多問:「這麼晚了還叫你特地去跑一趟?」
「司令明早要去濟南開會,過兩天才回來,大概是想趕著先把這事辦了。」
「那白副官,辛苦你一趟了,東西就這些。」
「好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