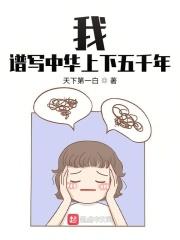车臣小说>平板车事故 > 第3章 哥我不想死(第1页)
第3章 哥我不想死(第1页)
那几天,我们兄弟两个天天喝酒,酒都是地方武装部和驻军送来的,每当有人来送酒的时候,小山都要反复跟他们说:这是俺哥,他是抗日英雄,他杀的鬼子能堆成一座小山。
人走之后,他会跟我说:俺哥,我就是你堆起来的小山!
那几天他老是跟我说:俺哥,我不想死!我死了,你就真的没有兄弟了。
那几天,我的鼻子特别酸,老想淌眼泪,又不知道是什么病。那个庸医宋麻子又得坑我的钱了。
我说:我给你当了9o多年的哥,没有我你早就死了十次都拐弯了,这是你欠我的,你下辈子得还我。
听我这么说,他就不觉得难过了:行,俺哥,这次我当排头兵,我先到那边探探情况,下辈子我给你当哥,啥都让着你!
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。
天亮的时候他的尸体被抬走了。我拄着拐棍送到村口。
走不动了,只能送到这了。
这让我想起了8o年前,我扛着歪了枪杆子的汉阳造跟着大部队转移的时候。小山光着脚丫子追到村口,那一年我15岁,他九岁,瘦得像一根豆芽菜。那年冬天很冷,他身上穿的破棉袄是我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,对他这个小个头来说衣服有点大,我用麻绳给他做了个腰带,不让风灌进去。
他那个时候对我高声喊:俺哥,你别死!打完仗就回来。
我跟排长说:借我两块大洋,一双鞋。
排长是一个四川人,个子很小,都没有步枪高。他一点都不抠门,就是说话难听:你娃不知道哪会儿就死了,你拿啷个还我?老子的布鞋还是我婆娘给我做的,我都舍不得穿。
我说:以后把给我的子弹都给你!
“你娃莫要耍赖!”排长当真借了我两块大洋,又极不情愿地从背包里抽出了一双布鞋塞给我。
我快折回去蹲在小山身边,布鞋对他来说有点大,只能给他别在腰带上,告诉他,再长高一点就能穿了。
我把大洋塞到他手里,告诉他:让俺爷给你换点杂面,够你吃两年的,过两年打完仗,哥给你带洋白面过来!
小山死活不要,哭着说:俺哥,我知道,这是你卖命的钱!我不要!
我拍了他脑门大声说:什么卖命,你哥我命大着呢,阎王爷还收不走!我得走了,鬼子来了,别往跟前凑。
排长催我快点走,6o军还在禹王山上阻击鬼子呢,他们撑不住多久,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
那时候我不懂,上头不是说仗打赢了么?那还转移个啥?说转移是好听一点的,其实就是逃跑。
那次离开村子,就开始了九死一生的战场生涯。幸运的是,我活着回来了。
我觉得自己能活够本,一定是借了我那些兄弟的命。
死人,太多的死人,这是我对那场战争最大的回忆,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一张张扭曲的死人脸,一双双临死都闭不上的眼,一片片被炸弹炸得不成样子的尸体,还有瘆人的哭喊声。